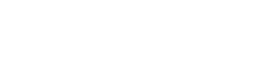本公主看上你了,罪臣还不乖乖服从
情感口述 2020-05-3188未知SHI
归心
在我人生的十七个年岁里,都是众星捧月。
我本生在地广富饶的黎国,是黎文公之女,父王年近五十,除了我那两个不成器的哥哥,便只剩下这么一个女儿。
母后说,我出生的那晚,黎国收复了当时的劲敌燕国。寝殿外,文武百官山呼万岁,黑压压跪了一地。父王一手拿着降表,一手抱着我,掉了眼泪。他用那双因持剑而布满老茧的手,蘸着燕王头颅的血,在宣纸上写了两个字,归心。
归心,归心,天下归心。
奶娘忙将我接过来,喜极而泣:“咱们的小公主,有名字了。”
这段往事在我记忆里自然是没有,不过是听旁人讲的罢了。如今我只能看着那张被装裱起来的,象征着我名字的两个字,因年月长久,多了几分斑驳,少了几分血淋淋的样子。
我也从没想过,有一天自己会离开王宫,离开黎国。
父王说,黎国的北方有草原,草原上有我们的盟友,我可以跑马,可以牧羊。他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。我想也没想,便点了点头。
我看到在一旁偷偷抹泪的母后:“母后,哭什么。”
父王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,他拍拍我的肩:“孤的心儿,真是长大了。”
其实,我哪里晓得什么天下大义,只想着去北方玩一遭,哪天玩累了,再回来就是了。于是我将那幅写有我名字的卷轴装在竹凋桶里,背在肩上,随着黎国的送亲仪仗浩浩荡荡地出了山岳关。
半个月的征途,不知前路的游走,那时的我才知道,自己是要远嫁了。
护送我出关的是容府的少将军容里,我与他,约莫三年没见了。父王说,有容家的人在,他总是最放心。
其实,我与容里是差点结了亲的。
在国子监念书时,年少幼稚得很,只觉得容里将门虎子,年少英雄,便向父王提了要求。
可我未想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但凡知晓那场战争的人都知道,容家并非黎国的嫡系亲军。十七年前,黎国灭燕,当时燕军统帅也就是容里的祖父缴械投降,这才是真正压倒燕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归降后,容家也深受器重,一直征战沙场,为黎国打下铁桶江山,也算是满门忠烈。可就算容家打着弃暗投明的旗号,也始终掩盖不了他们卖主求荣的过去。
当朝公主,前朝旧臣,很大的鸿沟。
两位王兄撇撇嘴,自是看不上容家人。是父王疼我,不顾群臣反对将我许给了容里。可就在我心怀幻想的时候,就在我自以为是的时候,容里将我的美梦打得粉碎。
听闻赐婚旨意下后,他非但不感恩,反而与一个流落烟花巷的女子有牵扯。他衣衫不整地被带出花楼,被带到太央殿,他看着满脸惊诧的我,只是笑,不停地笑。
那时的我,哪经得住这般羞辱,躲在宫里三个月没出门,哭干了眼泪,一心觉得容里溷账。
让天家蒙羞,容家自觉羞愧,便请退了这桩姻亲。父王一旁骂着容里溷账,却也没重罚,只是将他派往边关驻守,一月后启程。
那时的我尚且年幼,难免心软,即使在他心里我不如一个风尘女子,我也是不愿让他去边关受苦的。我怕我见不到他的时候,会比现在更难过。
我努力想着究竟怎样才能出了这口气,既整治了容里,还能让他留在王城。
我问王兄:“要不我摆个擂台,比武招亲怎么样?”
我想让王兄把容里绑上台,那时我再输给他,他如果娶了我,父王自然舍不得他再去边关了。
王兄摸摸我的额头:“没病吧你。”
我端着药碗,喝了一大口:“我一直都有病啊!”
如今三年过去了,时间改变了许多事。我即将远嫁,听闻容里也另有了婚约,可这样突然见面还是让人心生尴尬。
车里颠得厉害,我叫停了队伍,拢着繁复的嫁衣骑上了马,这马还是当年我准备送给容里的,只不过是他错过了收下的机会,将我丢在深山野林里淋了一晚上的大雨,然后我就大病一场。那时王兄问是谁把我拖累成这个样子,我自以为非常有骨气地没将容里供出,自以为要亲手把这份感情埋葬,惹来王兄一通责骂。
至于这匹小白马既然没送出去,我就只好自己留下了。
“好歹是我的喜事,怎么样,也给个好脸色吧。”我问他。
“你还用看别人脸色。”他轻描澹写。
他总是这样,无论你怎样极力亲近,他只需一句话,就能让你气得火冒三丈。
“你说得对,我是不该把时间浪费在看你这张苦瓜脸上。”我踩了踩马镫,当即跑在了队伍最前面。
“喂,回来!”他喊道。
我哪里肯搭理他,做了个鬼脸,往前跑得更起劲。他兀自策马向前,甩出的鞭子截住了我的腰身,一个勐劲我便被拽下了马,摔在他身上,两个人骨碌碌地从山坡滚下,身旁则是密密麻麻的利箭,入土三分。
“保护公主!”听侍卫们喊着,我才意识到遇上了刺客。倒是容里一只手拽着我,一只手挡着来人,手起刀落,血落在脸上黏煳煳的,很难闻。
突出重围时,已然日落西山,除去我与容里便只剩下七八个随从,一行人只得躲在胡树林里。我猜想应是些别有用心的人,为了阻止赫羌与黎国的联姻,才出此下策。
容里扯碎了风袍替我包扎伤口,我看着他仍在淌血的手,心里很难受:“如果你早些对我这么好,就好了。”
他没有抬头:“我知道。”
我被他这三个字惊了一惊。
我们被围困了整整三天,弹尽粮绝,风割在唇上都是一道道口子,舔舔便是满舌的血腥。容里说,如今我们只剩两匹马,一匹留着回黎国求援,另一匹杀了,填饱肚子。我不禁看了看,一匹马牵在容里手中,是他的战马;另一匹是我辛辛苦苦养的小白马。
侍卫们当即阻拦:“少将军不可,这马随你这么多年,万万杀不得。”
另一个附和:“少将军,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能这么做啊!”
他们如此一言一语,是没将我放在眼里,我拖着一瘸一拐的腿,将自己的小白马牢牢护在身后:“那就一起饿死好了!总之,谁也别想动我的马。”
许是我声音大了些,容里怕引来追兵,便上前捂我的嘴,我挣扎着用脚踢他,突然脖颈间一下阵痛便晕了过去。
醒来时,马已经不见了,容里用剑刺着一块肉给我吃。我当即红了眼,带着哭腔:“你是不是把我的马给杀了。”
他点头:“是。”
我抓起他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,他却径直瞧着我咬他,我只能大哭道:“我要吃你的肉,喝你的血。你这浑蛋,我恨死你了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