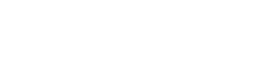最美的爱情,我们看不到,在车里撞了我八次高黄
6年前,她在一家电台主持夜间热线节目,节目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--《相约到黎明》。那时,她只有23岁,年轻大度,芳华逼人。每天清晨,她从电台的石阶上走下来,然后就在28路车的站台上等车。
很多次他和她都在这里相遇。那年,他方才来到这个都市,他是她忠实的听众。最初冲动他的是她的声音,闪电一般击中了他孤独的内心。
28路车的第一班车总在清晨的6:30开来。他选了她后排的一个位置,他默默地看着她,就像听她的节目。
对此,她却一无所知。她的男伴侣刚去日本,男伴侣24岁,一表人才,在一家日资公司做筹谋,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韩语。他去日本时,她送他,飞机从虹桥机场起飞,然后在天空中变得像一只放在橱窗里的模型,呼啸的声音还残留在她的耳边,她才把抑制了许久的泪水释放了。她不想让他看见她的脆弱,却有一种只有本身才气体会的痛。这是她第一次恋爱中的别离……她得恪守着本身的诺言,她对他说:“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,我城市等你……”她不是那种爱许诺的人。因为她真的很爱他才说了这句话。她不需要他对她答理什么,既然爱一小我私家,就应该给他最大的空间和自由。 28路早班车从都市的中心穿过,停停走走。她下了车,他也下了车,他看到她走进一栋20层的大厦,然后看到第11层楼的一扇窗粉红色的窗帘拉开了,她的影子晃过。他想,那些初升的阳光此时已透过她的窗户,然后落在她的脸上,一片绯红。
有一天,他拨通了她的热线电话。他问她:我很爱一个女孩子,但我并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我,我该怎么办?她的答案就通过电波传到他的耳际:报告她。爱不能错过。
第二天清晨,28路车的站台上,他早早地呈此刻那里。她从电台的石阶上走下来,他又坐在她的后排。车又在那栋20层的大厦前停了下来。他随着她下了车,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进了大门。因为没有措辞的理由、没有戏剧化的情节。他是那种很谨慎的男孩。他不想让她认为他很鲁莽。 终于有一天,车晚点了。后来他们才知道车在路上出了点故障。那时已是冬天,她在站台上等车,有点焦急。因为风大,她穿得很薄弱,她走过来问他:几点了?他报告了她准确的时间。站台上只有他们俩。她哈着寒气。他对她说:很喜欢你主持的节目。她就笑:真的?他说:真的,听你的节目已有一年了。他还说:我问过你一个问题的,但你不会记得。于是他就说了那个问题。她说:本来是你。就问他:后来你有没有报告那小我私家呢?他摇摇头说:怕拒绝。她又说:不问,你怎么会知道呢?她还报告他:我的男伴侣追我时,也像你一样。后来他对我说了,我就承诺了。此刻他去了日本,三年后他就回来…… 车来了,搭客也多了。在老处所,她下了车,这次他却没有下,心中的寒冷比冬天还深。
故事仿佛就这样该结束了。但在次年春天的一个午后,她承诺他去一家叫“惊鸿”的茶坊。因为他说他要分开这个都市,很想和她聊聊,聊完之后,他就会遗忘这个都市。她觉得这个男孩子满腹心思,有点痴情有点可爱,只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说他爱的人是她。她确实惊呆了,但还是没有接受。她说:不行能的,因为我对男伴侣说过: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,我城市等他……我们是没有可能的。他并没有觉得悲痛。很久以前他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。“我走了,恋爱留在这个都市里。”他说。 午后,冬天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大街上,他像一滴水一样在人群中消失了。
恋爱有时候就是这样:相遇了,是缘;散了,也是缘,只是浅了。她继续做她的热线节目。
她的男伴侣终于回国了,带着一位韩国济洲岛上的女孩。他约她出来,在曾常常见的处所。他神不守舍地说了一些天南地北的话。“我想和你说一件事……”他终于说。无奈的荒凉在那一刻迅速蔓延,像潮流一样,她只恨到此刻才知道。痴心付诸流水,只是太晚了。反水不收。 她请了一段时间的假,呆在家里,只是睡,太疲倦了。一起走过的大街,看过的街景,说过的话……爱过、疼过的故事都淡了。她心如止水地上班去。
其实,他并没有分开这个都市,只是不再乘28路车。他依旧听她的热线,是她最忠实的听众,甚至于有点沉沦从前的那种绝望。
有近一个星期,他没有听到她的声音,以为她出差了,或举行婚礼了……有些牵挂。
三年后,一个很偶然的机会,他读到她的一本自传--《晚上醒着的女人》。
书中写了她失败的初恋;也写了一个很像他的男孩,还有那家叫“惊鸿”的茶坊……那时他成婚刚一年,妻子是他的同事,一个很听话的女孩。
(实习编辑:吴瑾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