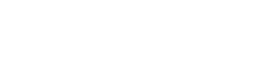"非典"幸存者口述:从那段经历中 我们能反思什么
婚姻恋爱 2024-04-12122网络

作为协和医院当年收治的最危重的“非典
”患者之一,礼露能活下来,是个奇迹。她一再说:“我的个人经历
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从这个经历
当中我们
能反思
出什么
来。”
口述
| 礼露
记者 | 李菁
看病
我经历的故事说起来很长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老记者叫陈寰,资历很老,从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,是一个有名的时政记者。陈寰阿姨是我父母在沈阳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,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,持续了60多年,直到我父母去世。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,我在北京工作以后,她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。
2003年4月初的时候,陈寰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,希望我能陪着她去。其实她也没什么
大事,只是已经86岁,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。她是高干身份,人民医院有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大夫,所以不像我们
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。
坦率地讲,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。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,说是广东的“怪病”已经跑到北京来了,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已经被封闭。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,没有公开,没有报道。这也难怪我弟弟听说后打电话过来,第一句话就问:“这个时候去医院,你不要命了?”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,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。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,我弟弟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,买了三十几个口罩——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,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。

4月7日一大早,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。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,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,还哈哈大笑。她是“老革命”,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,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,她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。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。
7点钟左右,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。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。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,那个人大约70多岁,高高大大的,声音洪亮,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,他已经开始咳嗽,也在发烧。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: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“那个病”,但先按“那个病”吃药吧。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——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,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,官方的说法是“非典
”,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。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,大家也都心照不宣,知道是指什么病。
2003年5月18日,北京市首支社区居民环境整治应急小分队在八宝山街道成立,负责社区的环境监督、清理和消毒
听段大夫说有可能是“那个病”的时候,我还是有点紧张。那间诊室连6平方米都不到,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,我和那个老干部离得特别近。他和段大夫面对面,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:“回去把口罩戴上吧。”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,但也是极为普通的那种。人民医院后来有100来个医护人员染上“非典”,不知道段大夫是否幸免。

陈阿姨做检查的时候,我就在医院里楼上楼下地跑,帮她挂号、取药、划价什么的,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,口罩时戴时摘。那天人民医院的人非常少,我还和陈阿姨开玩笑说:“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时候。”陈阿姨说:“既然清净,那就多看几科吧!”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内科、放射科和神经内科。一直忙到12点半,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。在呼吸内科外面的时候,旁边坐着一个戴口罩的女人,她发着高烧,还不停地咳嗽。
回家以后,我在网上看到了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写的那篇东西,我才知道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严重。但是人都有侥幸心理,总觉得去一趟医院就染上了?至于嘛!
8日那天没什么异常。9日那天特别暖和,大概都有20摄氏度了,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,把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,还是觉得冷。睡到半夜竟然冷醒了,在被窝里缩成一团。第二天一早,牙齿开始打颤,到了下午,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。体温计一量,接近39摄氏度。我想,坏了!可是又拼命否定:怎么就那么巧呢?全北京都没几人得。那时候媒体说,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,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,怎么就会是我呢。
当时我家里还借住着两个客人,一个是我的堂弟礼斌,我喊他“阿斌”,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来北京实习的新闻系学生万莹,她是经朋友介绍借住我家的。我让他们马上把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,然后让万莹把我动过的东西全部用酒精擦一遍消毒,让他们把牙刷也换掉。

我想到的第二件事,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例的资料。万莹很快就找到了,然后打印出来给我,其实当时找到的中文资料就只有一页纸那么多。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说此病目前没有对症疗法,一般情况下感染到肺部,出现肺炎,然后是发病5到7天后窒息死亡。这里面还有一句话,只是说这个病的“病程”一般是两周——这个在医学里究竟是什么意思,到了今天我还没十分清楚它的意思,但是它在后来给我很大精神上的支撑,因为我坚持到了第10天还没有死,我就想,这个病程是两周,我还有机会。
当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:应该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,少出去和大家接触。
五进五出
4月11日一早醒来,烧还是没有退,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,可还是禁不住浑身打颤。不过吃饭还好,精神也还好,也并没有咳嗽。4月12日情况依然没有变化。我还抱着幻想:发烧几天也是正常的,也一点咳嗽都没有,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,就在家挺着慢慢恢复吧。
可是到了13日这一天,我开始浑身疼,而且胸口开始有憋闷的感觉。我跟阿斌说:“不行,咱们得上医院!”阿斌的防范意识比较强,他不但戴了口罩,还穿了皮夹克,还戴上了墨镜。
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医院只一路之隔,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的急诊。当时医院里有很多病人,但是我发现医生们都没有戴口罩。医生让我先去化验血,结果是白血球低。然后做胸透。胸透显示,肺部没什么事。既然只是发烧,医生给我开了药,让我每天去打针。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了,现在一看这结果,一下子无比轻松起来,就像一块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被挪走了一样。从人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,我虽然还发着烧,但是那个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。

上一篇:17岁抑郁少女口述: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
下一篇:没有了